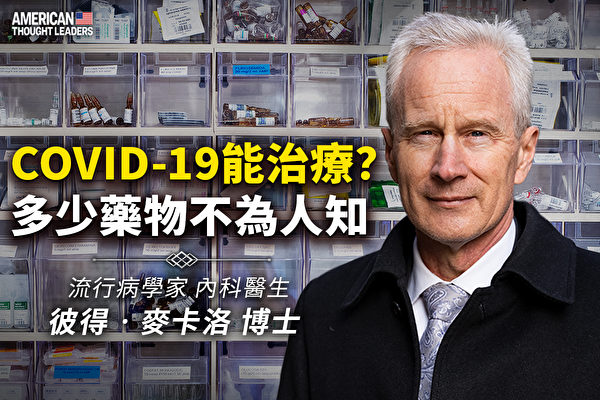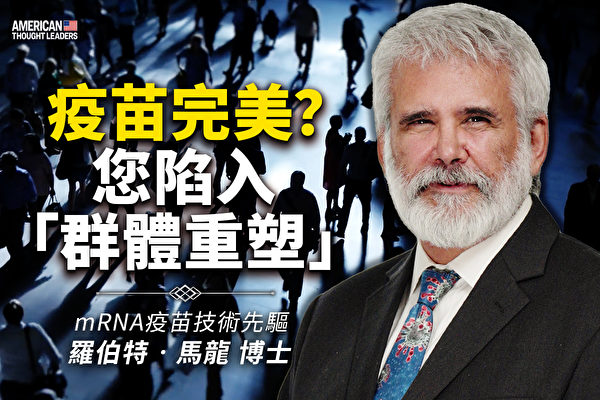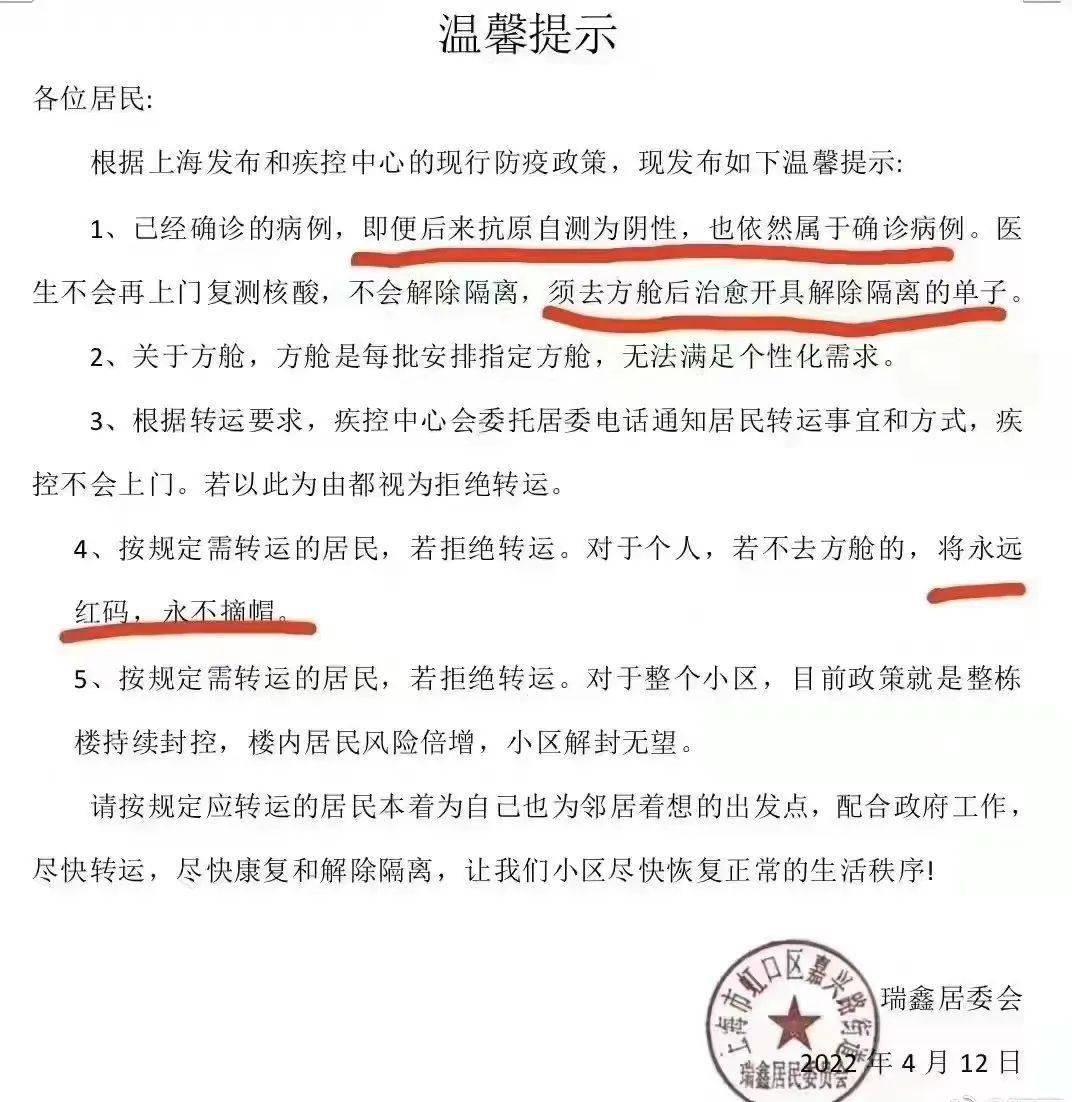“一直没有对新疗法进行月度审查。没有对疫苗的数据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月度审查。什么都没有。两年来,有关COVID-19的任何科学信息一直都对美国人束之高阁。”
在这个由两部分组成的访谈中,我们采访了内科医生、心脏病专家、流行病学家,也是第一篇关于早期COVID-19门诊治疗中涉及种药物方案的论文的主要作者彼得‧麦卡洛(Peter McCullough)博士。我们讨论了有关COVID-19治疗的全套证据,包括一种可能在孟加拉国消灭了COVID-19病毒的预防方法。
麦卡洛表示:“在乔杜里(Chowdhury)的治疗方案中,他们使用了稀释的聚维酮碘(povidone-iodine),实际上是在鼻子里杀死了病毒。”
第一部分,彼得‧麦卡洛博士谈到了对羟氯喹、伊维菌素和其它新冠疾病治疗药物的莫名其妙的压制。
随着人们对(接种疫苗引起)心肌炎和疫苗的其它影响的担忧日益增加,麦卡洛详细分析了他在疾控中心(CDC)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(VAERS)中看到的情况,以及这些数字的真正含义。VAERS系统的准确性如何?有多少报告可直接归因于COVID-19疫苗?
麦卡洛说:“在86%的情况下,没有其它解释。”
这里是 《美国思想领袖》节目,我是杨杰凯(Jan Jekielek)。
观看完整影片及文稿请至:https://www.youlucky.biz/atl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-
彼得·麦卡洛博士,欢迎你来到《美国思想领袖》节目。
麦卡洛:杨,谢谢你邀请我。
COVID-19无法治疗吗?
杨杰凯:我想,一直以来,很多人都对你要说的东西感兴趣,甚至是甚为感兴趣,那就是给COVID-19(我们大纪元称之为CCP病毒——中共病毒)提供治疗方法。你自己也用这些方法治疗病人,我认为,很多人可能不是太了解。那么,就请给我讲讲你实际的医疗实践吧。
麦卡洛:在过去两年里,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已经完成了一项新冠病毒的研究计划,之前,没有医生见过SARS-COVID-2病毒感染病例,也没有医生以前真正治疗过COVID-19病毒。
那麽,作为一个医生、一个涉猎广泛的医学专家,我一直在从事内科和心脏病学、成人疾病方面的研究和治疗。我不畏挑战,竭力治疗我的每一个高危病人,以避免住院和死亡这两种不良后果。
杨杰凯:这很吸引人,因为在大流行开始的时候,人们认为,除了住院之外,没有治疗手段。
麦卡洛:(对于新冠疾病)有一个假定,而且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假定。在医学界,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假定,说一种疾病在病人住院前阶段没有治疗方法,我从未见过一个大规模的假定,是不假思索做出的,而且是从一开始就做出的。从第一个病人开始,就有一个假定:在病人跨过门槛入住医院之前,这种疾病是无法治疗的。
那么,这个假定的背后是什么?我认为这个假定的背后是恐慌和自我保护。门诊、护士、其它卫生部门、医生实际上觉得,对他们来说,在住院前的阶段治疗病人相当有风险,而且有可能感染其他病人,对门诊、办公室、其它类型的治疗场所也造成感染风险。
因此,从某种意义上说,入院前治疗阶段(prehospital phase)被视为禁区。人们顺水推舟地辩解说:“这种病毒无法治疗,我真的很想治疗病人,只不过它根本无药可治。”但是他们从一开始便宣称无药可治,两年后仍然如此,我想每个人听了之后,都会明白,这个基本假设有点不对劲。
担任医学期刊《心肾医学》主编
杨杰凯:对这个问题,我有一大堆话要说,因为,至少有几种治疗方法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(FDA)批准了的。让我们稍后再谈这个问题,在此之前(先告诉我们您的背景),你实际上是一个主要医学期刊《心肾医学》(Cardiorenal Medicine)的主编。
我听说,你是这个领域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专家。而与此同时,你还在设法行医治疗COVID病人,你是如何做到的?这个临床实践过程是因为COVID爆发而启动的,还是之前就已经存在?
麦卡洛:是这样,我刚进入临床实践的第四个十年,也就是说,我维持了内科和心脏病学的委员会(每隔10年更新一次证书)的认证(已经四次了),(目前)我正处于美国内科医学委员会(ABIM) 这个“维持认证”(Maintenance of Certification,MOC)计划的第一年。实际上,我已经多次更新了内科的认证,每隔10年,都需要经过专业考核后重新认证,心血管疾病方面的认证也是如此。
在接受心脏病学培训之前,我曾有一段时间作为内科医生执业。此外,我还接受了流行病学的培训,这是关于疾病的分布和决定因素的研究。但从一开始,我的研究领域就是涉及多学科的研究,那就是研究心脏和肾脏,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激素和神经、生理化学系统,紧密地联系起来的。
这些系统对于医学诊断和治疗非常关键。因此,在心肾医学领域的一些发现,从某种意义上说,带进了这个(传染病)领域,对此许多人都做出了贡献。我有幸担任《心肾医学》的主编多年,该杂志的出版商是瑞士巴塞尔的Karger公司。
如今我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了,我担任《心血管医学评论》(Review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)的主编多年,这个杂志最初由MedReviews在纽约市出版。现在, 这个杂志了仍由MedReviews公司出版,该公司搬迁到香港,我现在已经和香港办公室合作多年了。那本杂志的影响因子一直在稳步增长。
我是第一版《心肾医学》(Cardiorenal Medicine)教科书的主编,也很荣幸地为布劳恩瓦尔德(Braunwald)的《心脏病学教科书》(Textbook of Cardiology)中撰写了一个章节,这本书被认为是心脏病学的圣经。我写的这一章的标题是 “心脏病和肾脏病之间的联系”。
在绝大部分医学生涯中,我是在世界各地作讲座。我曾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(NIH)、其它政府机构举办的会议作过讲座。我是NIH数据和安全监测委员会成员,参与了大型制药公司、体外诊断公司的临床试验,很荣幸地成为这些大型临床试验指导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。
我与心脏科、肾脏科和内科的同行医生都有合作,目标在于推动该领域的发展。在此过程中,我发表了660多篇经同行评审的论文,收录在国家医学图书馆(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)中。其中许多论文,我是为论文负责的第一或高级作者,有时我被刊载于作者的博客中,因为我是调查小组的成员。
增刊COVID-19治疗 或挽救数十万人生命
在我主编的《心血管医学评论》杂志中,单独做了一个COVID-19治疗增刊,我指派了一名编辑独立负责,这样就不会有利益冲突。在那篇论文中,我将作者范围扩大到57人,包括我自己。但我希望治疗过大量病人的医生能提供意见,他们正在治疗成千上万的病人,我希望所有不同类型的想法都能摆在桌面上。
这就是2020年12月发表在《心血管医学评论》上论文的前因后果,那篇论文的标题是“盘点COVID-19的序列多药治疗方法”(Sequence Multi-Drug Therapy for Inventory of COVID-19)。通过《美国医学杂志》和《心血管医学评论》,美国医生和外科医生协会(AAPS)创建了 《家庭治疗指南》(Home Treatment Guide)。
这成为我所知道的向公众提供的关于COVID-19的最多下载和利用的文件,已经被下载和分享了数百万次。可能避免了数千万人住院治疗,可能挽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。
杨杰凯:真是不可思议,因为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期,我们可以称之为大量信息、大量错误信息、虚假信息(充斥的时期)。有时很难知道哪些信息是真实的,哪些信息是可信的,哪些是不真实的?很高兴了解到这个《家庭治疗指南》,实际上是根据一篇经过严格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制定的,该论文的第二版在2020年(12月)问世。我直到此刻才知道。
麦卡洛:我们把尽可能多的参考文献、知识库继续扩大。因此,发表最多的治疗剂是最早使用的药剂,即羟氯喹(hydroxychloroquine),有超过300项支持性研究。
接下来是伊维菌素(Ivermectin),超过63项支持性研究。之后,我们有支持性的随机试验,对皮质类固醇(corticosteroids)进行了元分析(荟萃分析)。我们有前瞻性的队列研究(cohort studies,又译为群组研究,注:通过对某一特定患病或未患疾病的人群在一定时间内的观察,根据相关性来确定被观察对象疾病变化或患病的风险)。现在,还有一些关于抗凝血剂的有限随机试验,及对其它的抗炎药的研究。
许多人不知道,关于COVID-19最大、质量最高的前瞻性随机安慰剂临床试验,实际上是用秋水仙碱(Colchicine,注:一种抗炎药)做的,由蒙特利尔心脏研究所完成。这个试验被称为COLCORONA试验。质量之高,击败了所有其它的治疗性试验,极大地减少了住院和死亡率。
期刊发表只是传播信息 需要政府相关行动
挑战之一是,已发表的科学论文,同行评审后在期刊上发表,只是传播了信息(并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相关行动)。因此,当我们有了这些口服疗法,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,委托对世界各地(新冠)病人治疗进行持续评估审查。
作为一个公民,我个人的期望是,在这场危机中,我们的(医疗)机构每月都要向各个国家和广大民众通报治疗进展,每个月都应该更新。应该有一个彻底的审查,应该有一个详细、彻底、公开的审查。我们支付公共卫生官员工资的目的,就是因为这个。
杨杰凯:据我所知,实际上有两种药物,已经得到了FDA的批准,我之前提到过。(一个是)单克隆抗体(monoclonal antibodies),我听说它能降低Omicron(奥密克戎)的感染,关于Omicron病毒,等会儿我们再详细讨论。那么另一个就是氟伏沙明(Fluvoxamine),这个名字对吗?
麦卡洛:紧急使用授权程序的历史很有趣。以前,大概有5到10个紧急使用授权产品,在美国投入使用。紧急使用授权的规定是这样的,它属于一种紧急情况,我们需要一些授权,以便在某类政府或私人救护行动中,迅速使用某种产品,而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,执行批准上市的程序。
不要忘了,当药物上市时,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上市?因此FDA的许多活动,实际上与药物广告有关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包装说明书或标签,实际上是一种销售药物的监管许可。一种药物的产品适用范围(indications),实际上是用于广告性标签的。所谓的标签是广告商使用的,它是药品上的广告性标签。
产品适用范围不一定是说医生会如何使用该药品,但它基本上给制药公司画了一个界限,这就是标签的作用。紧急使用授权已经有了,所有这些都齐备了。现在只是一个问题,是否有足够的信息,来支持其使用?让我们把它拿出来。
对于最流行疾病的治疗、住院和门诊 两年后还是谜
时至今日,我们不知道哪家治疗COVID-19病人的医院死亡率最低,哪家医院死亡率最高,完全没有。因此,对于我们时代最流行疾病的治疗、住院和门诊,两年后还是一个谜。
杨杰凯:没有机构正在研究治疗方法吗?
麦卡洛:我很早就加入了一个合作团体,由哈佛大学医学院领导。2018年,我刚刚成为哈佛医学院的讲席教授,这是一个场面相当热闹的活动。我在肾脏病学和心脏病学的两个科系都做了讲座,一位年轻的肾脏病学家联系了我说,“我正在推动应对COVID病毒。” 我说,“太好了,你打算做什么?”
他说,“我正在组织一个合作团体,称为‘阻止COVID’(Stop COVID)”。我说,“太好了,我想报名参加,我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团体。”我们成立了机构审查委员会,我们组织了研究人员,我们尽可能参加“阻止COVID”活动。我接着说,“我们要做什么? ”他说,“我们要观察数据。” 我说,“我们要阻止COVID吗?”他说,“嗯,不,实际上就是到重症监护室(ICU),做一些观察性的记录。”
所以,的确如此,学术机构正在做观察,他们在观察这个病毒。但是不是要阻止COVID病毒,从未阻止过一例COVID感染,也从未阻止过一例死亡。而我们(的医院)没有进行任何有组织的、高质量的、创新的治疗方案,也没有宣称这样做,没有人这样宣称。医院应该积极招募病人参加独特的、开创性的治疗方案。
现在,不是有ACTIV(加快推进COVID-19治疗性干预和疫苗的开发)实验项目吗?是否有几百人参与了bamlanivimab试验和sotrovimab试验?是的。可能有近千人参与了瑞德西韦临床试验。可你知道,有多少个上百万、上千万的美国人被送进医院吗?该研究成果则微不足道。
我们从我们的(官方)机构听到的一件事是,“我们不建议在临床试验之外使用这些药物。”我说,“给我们安排临床试验”。我喜欢临床试验,我主持过临床试验,我在临床试验方面非常专业,我想要做临床试验。
哪里可以找到COVID-19的研究反馈?
2021年3月,当时我在德克萨斯州参议院作证,炮轰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(HHS)。我质问道,“哪里能找到1-800(免费)电话号码,这样,我们的老人可以取得这些临床试验(研究结果)? ”回答是,“他们可以网上浏览网站clinicaltrials.gov”。
我说,“为什么不设身处地想一想,一个75岁老人,发着高烧、呼吸困难,而那位老人必须要通过浏览clinicaltrials.gov,找到研究结果?”高速公路上的广告牌在哪里,上面写道:“1-800(免费)电话号码,COVID是一种糟糕的病毒?美国在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,这里有一个1-800(免费)电话号码,你可以取得研究成果。”没有这样的电话号码。
在哪里可以找到COVID-19的研究反馈?我们本应该在2020年初,就对住院和院前病人进行大型临床试验,什么都没有。我给你讲过,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曾有一次针对羟氯喹、阿奇霉素的(临床试验的)尝试,而在2000名病人中,他们找到了20人,然后(还没实施)就放弃了。
观看完整影片及文稿请至:https://www.youlucky.biz/atl